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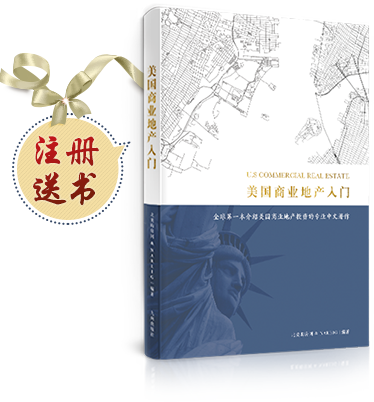
зЂВсВЂЭЈЙ§бщжЄМДПЩЛёЕУМлжЕ88дЊЁЖУРЙњЩЬвЕЕиВњШыУХЁЗ
вбгаеЫКХЃП ТэЩЯЕЧТМ ОМЭШЫзЂВс
ЮввбдФЖСВЂЭЌвтЁЖББУРЙКЗПЭјгУЛЇЪЙгУавщЁЗ
УРЙњИпаЃЕФЭЌадСЕЮФЛЏ
РДдДЃКhttp://www.danlan.org/disparticle_49093.htmзїепЃКББУРЙКЗПЭј

ЩЈвЛЩЈЃЌЫцЪБПД
ШЅУРЙњНЬЪщжЎЧАЃЌЭЌадСЕЕФВЪКчРыЮвЕФЩњЛюЛЙЪЎЗжвЃдЖЁЃЮвЩэБпЕФЭЌадСЕХѓгбУЧДѓЖрУЛгаГіЙёЃЌКмЖрЛЙеѕдњдкЩэЗнШЯЭЌЕФРЇЛѓжЎжаЃЌЩчЛсЖдЭЌадСЕЕФНгФЩЖШЫфгаЬсИпШДдЖВЛЙЛПЊЗХЁЃФЧаЉгыЭЌадАщТТЩњЛюдквЛЦ№КмОУЕФШЫЃЌЫцзХФъСфЕФдіГЄвдМАИИФИЕФДпЛщЃЌВЛЕУВЛзіГівЛИіМшФбЕФбЁдёЁЃгЩгкжаЙњЕФЗЈТЩВЂВЛдЪаэЭЌадЛщвіЃЌЫћУЧЕФбЁдёзЂЖЈЛсЪЙвЛаЉШЫЪмЕНЩЫКІЁЃ
ЁЁЁЁ2013Фъ10дТЕФвЛдђЛщбЖЪЙЮвЕквЛДЮИаЪмЕНЭЌадЛщвіРыЮвЕФЩњЛювВПЩвдКмНќЁЃЕБдТЃЌЭўСЎТъРібЇдК(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)ЧАЗУЮЪЖЪТЛсЖЪТНмИЅШ№·ЬиРУЗЖћ(Jeffrey Trammell)гыЦф36ФъЕФЭЌадАщТТдкУРЙњзюИпЗЈдКОйааСЫНсЛщвЧЪНЃЌзюИпЗЈдКЧАДѓЗЈЙйЁЂЭўСЎТъРібЇдКЧАУћгўаЃГЄЩЃЕТР·Дї·АТПЕФЩ(Sandra Day O'Connor)ЮЊЫћУЧжїГжСЫЛщРёЃЌетЪЧдкзюИпЗЈдКжСНёОйАьЙ§НігаЕФСНГЁЭЌадЛщРёжЎвЛЁЃЮвУРЙњЕФвЛаЉЭЌадСЕХѓгбдкЩчНЛЭјеОЩЯЛЖЯВЕиЗжЯэетвЛЯВбЖЃЌгкЫћУЧРДЫЕетЮовЩЪЧвЛИіеёЗмШЫаФЕФЯћЯЂЁЃ
ЁЁЁЁЕЋЪЧЃЌЯёЬиРУЗЖћЯШЩњетбљЕФЭЌадЛщвіРДЕУВЂУЛгаФЧУДШнвзЁЃжБЕН2004ФъЃЌТэШјжюШћжнВХГЩЮЊУРЙњЭЌадЛщвіКЯЗЈЛЏЕФЕквЛИіжнЁЃдк2014Фъ10дТ6ШезюИпЗЈдКвдЧПгВЕФзЫЬЌВЕЛиИїбВЛиЗЈдКЕФЩЯЫпжЎЧАЃЌУРЙњжЛга19ИіжнЪЕЯжСЫЭЌадЛщвіКЯЗЈЛЏ(ДЫЭтЃЌЛЊЪЂЖйИчТзБШбЧЬиЧјДг2010ФъЦ№вВдЪаэЭЌадЛщві)ЁЃЕУвцгкзюИпЗЈдКЕФПЊЕРЃЌНижС2014Фъ12дТГѕЃЌЙВ35ИіжнЪЕЯжСЫЭЌадЛщвіКЯЗЈЛЏЃЌЕЋФПЧАШдга15ИіжндкВЛЭЌГЬЖШЩЯНћжЙСЫЭЌадЛщвіЛђЦфЫћаЮЪНЕФЭЌадАщТТзщКЯЁЃ
ЁЁЁЁЭўСЎТъРібЇдКЫљдкЕФИЅМЊФсбЧжнвЛжБНЯЮЊБЃЪиЃЌЕБЬиРУЗЖћЯШЩњНсЛщЪБЛЙЭъШЋНћжЙЭЌадЛщвівдМАШЮКЮаЮЪНЕФЭЌадМвЭЅЁЃОЁЙмжнеўИЎзд1969ФъвдРДОЭДђГіСЫ“ЧщШЫжЎжн”ЕФаћДЋгяЃЌетРяЕФ“ЧщШЫ”ШДХХГ§СЫЭЌадАщТТЁЃвђДЫЃЌ2012ФъЮвГѕЕНИУаЃШЮНЬЪБЃЌЖдаЃдАжаДІДІЭИТЖзХ“ЭЌадСЕгбКУ”ЕФаХЯЂИаЕНЪЎЗжВявьЁЃ
ЁЁЁЁЮвдкбЇаЃЕФЖрИіГЁКЯгіМћЙ§ЬиРУЗЖћЯШЩњЃЌжЊЕРЫћдјдкЙњЛсЩНЮЊУёжїЕГаЇСІЪ§ЪЎдиЃЌЕЋВЂВЛжЊЯўЫћЕФЭЌадСЕепЩэЗнЁЃЬиРУЗЖћЯШЩњгк1973ФъБЯвЕгкЭўСЎТъРібЇдКРњЪЗЯЕЃЌдкаЃЦкМфдјШЮбЇаЃРКЧђЖгЖгГЄЁЃдкЩЯЪРМЭ70ФъДњЃЌЭЌаджЎМфЕФНЛЭљЛЙЪЎЗжЮЃЯеЁЃЫћЕФбЇЩњДїЮЌ·ТѓЛљЯЃПЫдквЛЦЊЮФеТжаЛивфЃЌЕБвьадСЕЭЌбЇРДЭљЩѕУмЕФЪБКђЃЌФъЧсИпДѓЫЇЦјЕФРКЧђЖгЖгГЄВЛЕУВЛ“АбздМКТёдкЪщКЃжа”ЃЌвђЮЊЫћЩюжЊ“ШЮКЮЕФНЛЭљКЭгеЛѓЖдздМКЕФУћЩљЖМЪЧжТУќЕФ”ЁЃ
ЁЁЁЁШЛЖјШ§ЫФЪЎФъЙ§КѓЃЌвЛЧаЖМВЛвЛбљСЫЁЃ2005ФъЃЌЭўСЎТъРіЬсУћЬиРУЗЖћНјШыСЫИУаЃЕФЗУЮЪЖЪТЛсЃЌетЪЧШЋУРжјУћИпаЃжаЕквЛЮЛЙЋПЊадЯђЕФЗУЮЪЖЪТЛсГЩдБЁЃДїЮЌИаЬОЕРЃК“етМўЪТУЛгаЗЂЩњдкНЃЧХЁЂВЎПЫРћЛђепТѓЕЯбЗЃЌЖјОЙШЛЪЧдкИЅМЊФсбЧЕФЭўСЎЫЙБЄЁЃ”
ЁЁЁЁЭЌбљСюШЫОЊбШЕФЪЧжкЖрбЇЩњПкжаСїДЋЕФЭўСЎТъРіЕФБ№КХЁЃ1693ФъЃЌЭўСЎТъРібЇдКгЩЕБЪБЕФгЂИёРМЭўСЎЙњЭѕШ§ЪРКЭТъРіЭѕКѓЖўЪРНЈСЂЃЌгІДЫЕУУћЁЃКѓРДЮвЕУжЊбЇаЃЛЙгавЛИіБ№ГЦ——“ЭўСЎЃІРРя”(William & Larry)ЃЌаЃУћБЛЯЗкЪЕиИФГЩСЫСНИіФаадУћзжЃЌАЕжИИУаЃЭЌадСЕЮФЛЏХЈКёЁЃ
ЁЁЁЁ2013Фъ9дТИУаЃе§ЪНГЩСЂСЫвЛИігЩЭЌадСЕбЇЩњМАЦфжЇГжепзщГЩЕФСЊУЫзщжЏЃЌУќУћЮЊ“ЭўСЎЃІРРя”ЃЌжМдкДгжнеўИЎКЭбЇаЃСНИіВуУцРДЬсИпШЫУЧЙизЂЯжДцЦчЪгЭЌадСЕЕФЗЈЙцКЭеўВпЕФвтЪЖЃЌгЮЫЕжнвщЛсжЇГжЭЌадСЕШЈРћВЂЗЯГ§ЯжДцЦчЪгадЗЈЙцЁЃИУзщжЏдМгаСНАйУћзЂВсГЩдБЃЌКИЧБОПЦЁЂЫЖЪПКЭВЉЪПЩњЃЌЙ§АыГЩдБЮЊЗЧЭЌадСЕепЁЃ
ЁЁЁЁ“ДгбЇаЃЕФеўВпВуУцРДПДЃЌЭўСЎТъРіЛЙДІдк20ЪРМЭЃЌЖјВЛЪЧ21ЪРМЭЁЃ”ПЫРяЫЙЕйАВ·БДЖћ(Christian Bale)ЫЕЁЃБДЖћЪЧ“ЭўСЎЃІРРя”ЕФДДЪМШЫМАЯжШЮжїЯЏЃЌвВЪЧИУаЃЙЋЙВеўВпзЈвЕЕФвЛУћбаОПЩњЁЃдкЙ§ШЅЕФвЛФъжаЃЌ“ЭўСЎЃІРРя”зщжЏСЫЖрЯюЮФЛЏЛюЖЏКЭНВзљЃЌбнНВМЮБіАќРЈжнвщдБКђбЁШЫМАЯрЙиСьгђЕФНЬЪкЃЌвддкШЋаЃЗЖЮЇФкЬсИпШЫУЧЖдЭЌадСЕШЈРћЕФЙизЂЁЃ
ЁЁЁЁБДЖћВЂВЛЪЧЭЌадСЕепЃЌЫћГЦздМКЫљзіЕФвЛЧаЪЧЮЊСЫЪЙЭЌадСЕГЃЬЌЛЏЃЌЮЊЭЌадСЕепељШЁЦНЕШЕФШЈРћЁЃ“LGBT(ХЎЭЌадСЕЁЂФаЭЌадСЕЁЂЫЋадСЕЁЂПчадБ№еп)ШКЬхгІЕБЯэгаЦНЕШЕФШЈРћЃЌжнеўИЎКЭбЇаЃЕФеўВпашвЊЪзЯШЗДгГетвЛЦНЕШадЁЃШчДЫЃЌШЫУЧЕФЙлФюВХФмИќПьЕиЕУЕНИФБфЁЃ”БДЖћЫЕЁЃ
ЁЁЁЁ“ЭўСЎЃІРРя”дкЖЬЪБМфФкШЁЕУСЫЯджјЕФГЩЙћЁЃЭЈЙ§гыаЃГЄАьЙЋЪвЕФВЛЖЯЙЕЭЈЃЌбЇаЃвбе§ЪНаое§СЫИУаЃЕФЗДЦчЪгеўВпЃЌдіМгСЫЙигкадЯђКЭЩэЗнШЯЭЌЕФЯрЙиЬѕР§ЁЃ2014ФъГѕЃЌ“ЭўСЎЃІРРя”ЫЕЗўСЫЭўСЎЫЙБЄЪаГЄЙЋПЊЗДЖдБЫЪБИЅМЊФсбЧжнНћжЙЭЌадЛщвіЕФЗЈАИЃЌВЂГяЛЎГіЬЈИУЪажЇГжЭЌадЛщвіЕФЬѕР§вдЗДЖджнФкЕФНћСюЁЃ
ЁЁЁЁ2014Фъ10дТЃЌдкзюИпЗЈдКЕФПЊЕРЯТЃЌИЅМЊФсбЧжнЪЕЯжСЫЭЌадЛщвіКЯЗЈЛЏЁЃдкЗЈАИЩњаЇЕФЕквЛЬьЭэЩЯЃЌ“ЭўСЎЃІРРя”дкаЃдАРяОйааСЫЧьзЃЭэЛсЁЃ“ИааЛУПвЛИіМсГжВЛаИЕФФуЃЌЪЧФуУЧГЩОЭСЫНёЬьЃЌ”ЬиРУЗЖћдкКиаХжааДЕРЃЌ“250ФъЧАЃЌЮваЃЫЙФЊЁЂЭўЫМНЬЪкЮЊНмьГбЗПЊЦєСЫЙигкЦєУЩКЭЬьИГШЫШЈЕФДѓУХЃЌШУЫћдк33ЫъФЧФъаДЯТ‘ШЫШЫЩњЖјЦНЕШ’ЃЌЫћЕФдЖМћдкНёШеЕУвдЭъЩЦЃЌЮЌЛЄСЫЫљгаLGBTЙЋУёЕФШЈРћЁЃ”
ЁЁЁЁШЛЖјЃЌЮвВЂВЛЯыАбУРЙњЕФаЃдАЬьецЕиУшЛцГЩвЛИіЭЌадСЕбЇЩњЕФЬьЬУЁЃгЩгкУПИіжнЖдЭЌадСЕЕФНгФЩГЬЖШВЛЭЌЃЌИїжнЕФаЃдАЭЌадСЕЮФЛЏздШЛГЪЯжГіВЛЭЌЕФФЃбљЁЃвЛЯюЛљгкЮЪОэЕїВщЁЂЩчНЛЭјТчаХЯЂКЭЪЙгУGoogleЫбЫїЪ§ОнЕФбаОПЗЂЯж(Мћ2013Фъ12дТ7ШеЁЖХІдМЪББЈЁЗЕФБЈЕР)ЃЌУРЙњжСЩйга5%ЕФФаадЪЧЭЌадСЕеп(дквдЭљИїРрбаОПжаЃЌетвЛБШР§ЭЈГЃдк2%жС10%жЎМф)ЃЌЦфжаЪ§АйЭђЕФФаЭЌадСЕепдкФГжжГЬЖШЩЯЛЙУЛгаГіЙёЁЃ
ЁЁЁЁЪ§ОнЗжЮіЯдЪО(Мћ2013Фъ12дТ8ШеЁЖХІдМЪББЈЁЗЕФБЈЕР)ЃЌжнФкЖдЭЌадСЕЕФНгФЩГЬЖШЖдЭЌадСЕЪЕМЪБШР§гАЯьНЯаЁЁЃР§ШчЃЌдкЭЌадСЕНгФЩЖШЗЧГЃИпЕФвЛаЉжн(ЦфжаЃЌТоЕТЕКжнзюИп)ЃЌЫНЯТЫбЫїЙ§ФаЭЌадСЕЭМЦЌЕФФаадБШР§ЪЧ5.4%ЃЌЖјдкНгФЩЖШзюЕЭЕФФЧаЉжн(ЦфжаУмЮїЮїБШжнзюЕЭ)ЃЌетвЛБШР§вВФмДяЕН5.2%ЁЃвВОЭЪЧЫЕЃЌдкФЧаЉЭЌадСЕНгФЩЖШНЯЕЭЕФжнФкЃЌЭЌадСЕепВЂУЛгавђДЫЖјМѕЩйЃЌЕЋЫћУЧУцСйЕФРДздЩчЛсКЭМвЭЅЕФбЙСІдђвЊДѓЕУЖрЁЃ
ЁЁЁЁ2005ФъЃЌРюЫМка(Stephen Leonelli)ЛЙЪЧИЅМЊФсбЧДѓбЇЕФДѓвЛаТЩњЃЌФЧФъЫћЯђИИФИЬЙАзСЫздМКЪЧЭЌадСЕепЃЌетЖдгкЬьжїНЬМвЭЅРДЫЕМђжБФбвджУаХЁЃИИФИЕБЪБЕФОЊВяЁЂОкЩЅКЭЕжПЙШдРњРњдкФПЁЃ“ЫћУЧУЛгаАьЗЈРэНтетжжЪТЃЌвђЮЊЭЌадСЕВЛдкЁЖЪЅОЁЗЕФНЬЬѕжЎФкЃЌЫћУЧвВКІХТЮвЛсИаШОАЌзЬВЁЁЃ”ЫМкаЫЕЁЃ
ЁЁЁЁжЎКѓЫМкаЕФДѓЙУЕФГіЙёСюетИіДЋЭГЕФЬьжїНЬМвЭЅвтЪЖЕНЭЌадСЕЦфЪЕРыЫћУЧВЂВЛвЃдЖЁЃ“дкДѓШ§ФЧФъИИЧзЯђЮвЕРСЫЧИЃЌЛЙдМЮввЛЦ№ШЅЭЌадСЕОЦАЩЁЃ”ЪБИєЖрФъЃЌЫМкаШдВЛНћИаПЎЃЌ“етЪЧзюСюЮвИаЖЏЕФвЛПЬЁЃ”дкаЃЦкМфЃЌЫМкаМгШыСЫбЇаЃЕФ“ПсЖљгыСЊУЫааЖЏзщ”ЃЌЛ§МЋељШЁЭЌадСЕШЈвцЁЃ2010ФъжС2013ФъЃЌЫћРДЕНББОЉЭЌжОжааФЃЌзщжЏЭЌадСЕШЈвцНВзљКЭЗжЯэЛсЃЌПЊЗЂЭЌадСЕЩчШКЛюЖЏМАаФРэНЁПЕЯюФПЃЌвдАяжњжаЙњЕФЭЌадСЕШКЬхЁЃ
ЁЁЁЁжаЙњЕФЭЌадСЕШЫШКЪЧБЛБпдЕЛЏЕФШѕЪЦШКЬхЃЌЕБУРЙњКЭЦфЫћвЛаЉЙњМвж№НЅгРДЭЌадЛщвіКЯЗЈЛЏЕФЭЌЪБЃЌжаЙњЕФЭЌадСЕШКЬхЛЙдкељШЁзюЛљБОЕФШЈРћЃЌБШШчЕУЕНз№жиЁЃ1949ФъвдРДЃЌЭЌадСЕШКЬхЪмЕНСЫЙйЗНКЭЩчЛсЕФЫЋжибЙжЦЁЃЩчЛсбЇМвРювјКгдкЁЖаТжаЙњадЛАгябаОПЁЗвЛЪщжаИХРЈСЫЙйЗНЖдД§ЭЌадСЕЕФЬЌЖШЃК“65ФъРДОРњСЫДгЛљБОЩЯШЋЪЧИКУцЗёЖЈЬЌЖШЕНжаадПЭЙлЬЌЖШЕФзЊБфЁЃ”1997ФъЃЌЭЌадСЕЕУвдЗЧзяЛЏЁЃ2001ФъЃЌЭЌадСЕДгОЋЩёВЁУћЕЅжаЕУвдШЅГ§ЁЃЕЋЭЌадМвЭЅдкЗЈТЩВуУцЕУЕНБЃЛЄетвЛуПуНЃЌЛЙвЃвЃЮоЦкЁЃ
ЁЁЁЁЙубраФ(Kayleigh Madjar)вВвЛжБЙизЂжаЙњЕФLGBTШКЬхЃЌ2014ФъЫ§БЯвЕгкУРЙњЮїББДѓбЇбЧжобаОПзЈвЕЃЌДѓЫФЪБПЊеЙСЫвЛЯюЙигкжаЙњЭЌадСЕРњЪЗЧїЪЦЕФбаОПЁЃбраФЫЕЃК“ЕБЮвУЧАбжаЙњЕФЭЌадСЕИХФюгыУРЙњ/ЮїЗНЕФИХФюНјааБШНЯЕФЪБКђЃЌетИібаОППЮЬтОЭБфЕУЗЧГЃгаШЄЁЃ”
ЁЁЁЁдкжаЙњЙХДњЃЌЭЌадСЕЯжЯѓвЛжБЖМДцдкЃЌЩчЛсвЛАувВГжПЊЗХЬЌЖШЁЃЯрБШжЎЯТЃЌОЁЙмЕБНёжаЙњЩчЛсЖдЭЌадСЕЕФНгФЩЖШдкВЛЖЯЬсИпЃЌЬиБ№ЪЧдкДѓГЧЪаЃЌЕЋЪЧЦеБщРДЫЕЭЌадСЕЛЙЪЧУєИаЕФЛАЬтЁЃжаЙњДѓЖрЪ§ЭЌадСЕепЦШгкМвЭЅКЭЩчЛсбЙСІВЛдИЙЋПЊадШЁЯђЃЌвђДЫвВДпЩњСЫГфТњЮЪЬтЕФ“аЮЪНЛщві”КЭ“ЭЌЦо”ЁЃРювјКгдкНгЪмЁЖХІдМЪщЦРЁЗЕФВЩЗУжаЬсЕНЃЌЕїВщЗЂЯжУРЙњ90%ЕФЪмЗУепГжЗДЖдЛђжЇГжЭЌадЛщвіЕФУїШЗЬЌЖШЃЌЖјжаЙњЕФЪмЗУепОјДѓВПЗжВЂУЛгаУїШЗЕФЬЌЖШЁЃдкжаЙњЃЌжЛвЊЭЌадСЕВЛЗЂЩњдкздМКЕФМвЭЅГЩдБжаЃЌШЫУЧвЛАуВЛЛсдквтетИіЛАЬтЁЃНќМИФъЃЌЫцзХАЌзЬВЁЮЪЬтЪмЕНШЫУЧЕФЙизЂЃЌжаЙњЭЌадСЕШКЬхЕФЩњЛюЕУЕНСЫИќЖрЕФЦиЙтЃЌШЛЖјВЛавЕФЪЧЃЌЭЌадСЕвщЬтвВвђДЫБЛАЌзЬВЁАѓМмЁЃ
ЁЁЁЁдкЮїББДѓбЇLGBTзЪдДжааФЪЕЯАЪБЃЌбраФЛ§МЋВЮгыСЫзЪдДжааФЕФИїЯюЛюЖЏЃЌдкШЋаЃЗЖЮЇФкЮЊLGBTШКЬхДДдьСЫжюЖр“АВШЋПеМф”ЁЃзЪдДжааФЮЊжЇГжЭЌадСЕЪІЩњЬсЙЉЯрЙиЕФжЊЪЖНЬг§ЃЌВЂЙФРјДѓМвдкЫоЩсЛђАьЙЋЪвЕФУХЩЯеХЬљ“АВШЋПеМф”БъжОЕФЬљжНЃЌЛЖгLGBTГЩдБгыЫћУЧНЛСїЁЃОнбраФНщЩмЃЌЮїББДѓбЇ2010ФъЕФЕїВщЯдЪОЃЌИУаЃ10%ЕФЪІЩњГаШЯздМКЪЧLGBTГЩдБЁЃ
ЁЁЁЁГ§СЫзщжЏЛюЖЏЭтЃЌИУзЪдДжааФвВСІЭМИФБфбЇаЃЕФеўВпЁЃНќФъРДЃЌетвЛзщжЏВЛЖЯЯђбЇаЃНЬЮёДІгЮЫЕдЪаэИќИФвбАфЗЂбЇЮЛжЄЩЯЕФаеУћ(адБ№Вювь)ЃЌВЂЯђбЇаЃЪЉбЙНЈСЂадБ№ПЊЗХЕФЫоЩсКЭЮРЩњМфЁЃ“вЊШУЙмРэВуИФБфеўВпКЭЙлФюЪЧвЛМўЗЧГЃФбЕФЪТЁЃ”браФЫЕЁЃОЙ§гЮЫЕЃЌОЁЙмбЇаЃПМТЧдкаТНЈЛђаТзАаоЕФНЈжўФкЮЊLGBTШКЬхаоНЈБивЊЕФЩшЪЉЃЌЕЋШдШЛВЛдИдкОЩНЬбЇТЅЛђЫоЩсдіЩшжаадЮРЩњМфЁЃ
ЁЁЁЁбраФБОШЫВЂЗЧЭЌадСЕепЃЌЕЋЫ§ЕФИчИчгыИпжаКУгбЪЧLGBTГЩдБЁЃ“Г§ШЅетвЛИіШЫдвђЃЌЮввЛжБМсаХадШЁЯђЪЧвЛжжЛљБОШЈРћЃЌЮвЮоЗЈРэНтЮЊЪВУДвЊЗДЖдЭЌадСЕЃЌ”Ы§ЫЕЃЌ“ШЫУЧе§дкж№НЅНгЪмЭЌадСЕЃЌЕЋЪЧЫћУЧВЛЛсеОГіРДДњБэLGBTШКЬхЙЋПЊЖдДЫБэЪОжЇГжЁЃ”Он2013Фъ6дТЦЄгШбаОПжааФЗЂВМЕФвЛЗнБЈИцЃЌШЋУР72%ЕФЪмЗУепШЯЮЊЭЌадЛщвіКЯЗЈЛЏЕФЧїЪЦвбВЛПЩБмУтЁЃ
ЁЁЁЁПЙељвдИФБфЃЌДѓЕжПЩвдИХРЈУРЙњаЃдАжаЭЌадСЕШКЬхЕФећЬхзДПіЁЃЖјдкФГаЉЬиЪтЕФЛЗОГЯТЃЌвЊЯыгРДИФБфЃЌетжжПЙељОЭБиаыИќЮЊГжОУКЭМЄСвЁЃдкЬьжїНЬбЇаЃЃЌЭЌадСЕЮЪЬтЯдЕУгШЮЊЭЛГіЁЃ
ЁЁЁЁ2013ФъЯФЃЌЕБЧЧжЮГЧДѓбЇЕФбЇЩњдкетЫљШЋУРзюЙХРЯЕФЬьжїНЬДѓбЇЕФаЃдАРяНгСњДЉЙ§вЛЩШЯѓеїадЕФЙёУХКХейЭЌадСЕбЇЩњГіЙёЕФЪБКђЃЌЫћУЧвЛЖЈУЛгаЭќМЧжБЕН1987ФъИУаЃЕФЭЌадСЕбЇЩњзщжЏЭЈЙ§ЩЯЫпВХЛёЕУСЫгыЦфЫћбЇЩњзщжЏЭЌЕШЕФШЈРћЃЌЖјЗЈЭЅЭЌЪББэЪОЧЧжЮГЧДѓбЇЮоашИјИУбЇЩњзщжЏ“аЃМЖШЯПЩ”ЃЌвђЮЊ“етбљзіЛсАЕЪОбЇаЃжЇГжЭЌадСЕЖјЮЅЗИЬьжїНЬЕФНЬЬѕ”ЁЃ
ЁЁЁЁдкУРЙњЃЌЙВгаСНАйЖрЫљЬьжїНЬДѓбЇКЭбЇдКЃЌЬьжїНЬжабЇдђГЌЙ§вЛЧЇЫљЁЃ2013ФъЕзЃЌСНЫљЬьжїНЬИпжаЕФвЛжТОйДыШУЮвУЧЧхЮњЕиПДЕНЃЌВЪКчЕФЙтЛдВЂЮДеевЋЕНећИіУРЙњДѓТНЁЃдкБіЯІЗЈФсбЧжнЃЌвЛЮЛдквЛЫљИпжаШЮНЬГЄДя12ФъЕФНЬЪІвђгыЦфЭЌадАщТТЩъЧыНсЛщжЄЖјБЛНтЙЭЁЃЮоЖРгаХМЃЌЮїбХЭМЖЋНМвЛЫљЬьжїНЬИпжаЕФИБаЃГЄвВвђгыЦфЭЌадАщТТНсЛщБЛбЇаЃЧыЭЫЁЃжкЖрбЇЩњАеПЮдкаЃдАФкгЮааПЙвщЃЌИпКА“ИФБфНЬЛс”ЁЃ
ЁЁЁЁНЬЛсЕФШЗЕНСЫИФБфЕФЪБКђЁЃНЬЛЪЗНМУИїдквЛДЮВЩЗУжажБбдНЬЛсЙ§Зж“ГСУдгк”ЭЌадСЕКЭЖщЬЅЕШЮЪЬтЃЌЖјКіТдСЫЦфИќДѓЕФЪЙУќ——“ЬьЯТвЛМв”ЁЃ
ЁЁЁЁ“етИіЪРНчЁЂетаЉДѓбЇашвЊНЬЛсЃЌЯждкШчДЫЃЌвЛАйФъКѓвВЪЧЃЌ”ЧЧжЮГЧДѓбЇЪзЮЛЙЋПЊЭЌадСЕепЩэЗнЕФбЇЩњЛсжїЯЏФкЬи·ЕйШјИУаЃаЃБЈЩЯаДЕРЃЌ“ЕЋЪЧЩчЛсдкИФБфЃЌЩЯЕлвВдкетжжИФБфжЎжа——ЧыВЛвЊОмОјЫќЁЃ”
ЁЁЁЁДЋЭГЙЬШЛживЊЃЌЕЋЮвУЧВЛФмОмОјИФБфЁЃЖЬЖЬЪЎФъЃЌдкжЇГжЭЌадЛщвіШЫЪПЕФВЛЖЯПЙељжЎЯТЃЌОЁЙмТЗЭОЧњелЃЌУРЙњЩчЛсКЭаЃдАЖМШЁЕУСЫвЛаЉЪЕжЪадЕФГЩЙћЁЃЬиРУЗЖћЯШЩњдкЖСБОПЦЦкМфЛЙашвЊЩюВиЙёжаЃЌЖјШчНёЫћШДПЩвддкзюИпЗЈдКЧЃЦ№АЎШЫжЎЪжЃЌЫћЕФФИаЃвВПЩвддкЙйЗНЭјеОЩЯНОАСЕиЯзЩЯзЃИЃЃЛОЁЙмФПЧАЛЙга15ИіжнНћжЙЭЌадЛщвіЃЌЕЋЮвУЧПДЕНзюИпЗЈдКдкжЇГжЭЌадЛщвіКЯЗЈЛЏетвЛЮЪЬтЩЯЕФОіаФЃЛЬьжїНЬМвЭЅГіЩэЕФЫМкадкГіЙёКѓеебљБЛИИФИНгЪмЃЌШчНёЫћвбЪЧЙўЗ№ДѓбЇПЯФсЕЯеўИЎбЇдКЕФвЛУћЫЖЪПЩњЃЌе§дкЛ§МЋЕиЮЊLGBTШКЬхељШЁИќЖрЕФШЈРћЃЛОЁЙмВПЗжЬьжїНЬШЫЪПдкЭЌадЛщвіКЭЩњг§ЮЪЬтЩЯЬЌЖШМсОіЃЌЕЋЪЧвВгаКмДѓвЛВПЗжЬьжїНЬЭНжЇГжЭЌаджЎАЎЁЃвђДЫЃЌдкЭЌадСЕЮЪЬтЩЯЃЌЮвУЧгІЕБИќЮЊПэШнЃЌИќМгЛ§МЋЕиВЮгыЖдЛАЃЌвВгаРэгЩИќЮЊРжЙлЕиЦкД§ВЪКчЦьПЩвдздгЩЕиЦЎбядкЪРНчЕФУПИіНЧТфЁЃ
ЁЁЁЁЮвдкКмЖрЕиЗНМћЙ§ОјУРЕФВЪКчЃЌЕЋзюУРЕФФЧЕРдквЛЪзИшРяЁЃ2012ФъЯФЃЌЮвгывЛЮЛУРЙњИшЪжПЊГЕааЪЛдкИЅМЊФсбЧЕФЙЋТЗЩЯЃЌгыЫћвЛЦ№жЦзїзЈМЕФИшЪжДђРДЕчЛАзЃКиЃЌЫЕЕРЃК“ЮЊСЫЪРНчЕФКЭЦНгыЦНЕШЃЁ”ЮвДѓаІЃЌБэЪОЫћУЧЙ§гкалаФзГжОЁЃЫћДгГЕРяевГівЛеХвдЧАЕФзЈМЃЌетеХзЈМЕФЫљгаЪеШыЖМОшИјСЫвЛИі24аЁЪБШШЯпЕчЛАЯюФПЃЌЮЊгаздЩБЧуЯђКЭЦфЫћЮЃЛњЕФЭЌадСЕЧрЩйФъЬсЙЉзЩбЏгыИЩдЄЁЃзЈМжагавЛЪзЫћаДЕФЭЌУћИшЧњ“Indigo”ЃЌЧр(ЕхРЖ)ЃЌДњБэЕФе§ЪЧетаЉЧрЩйФъЁЃ
ЁЁЁЁ“ШчЙћФЧаЉЪмШЫЛЖгЕФКЂзгЪЧКьЩЋЁЂТЬЩЋКЭЛЦЩЋетаЉжївЊбеЩЋЃЌЮвУЧбЁдёЕФЪЧВЪКчжаВЛдѕУДЪмЛЖгЕФЧрЩЋЃЌЕЋЫћУЧвЛбљживЊЃЁдкетИіЪРНчЩЯЮвУЧЖМЪЧВЛвЛбљЕФЃЌЫљвдЮввЊГЋЕМЦНЕШЁЂСІСПКЭНгЪмЁЃ”ХѓгбПДзХЧАЗНМсЖЈЕиЫЕЁЃЫћАДЯТВЅЗХМќЃЌвєРждкГЕФкЛиЯьЃК
ЁЁЁЁ“ашвЊЫљгаетаЉбеЩЋЃЌВХФмНЈдьвЛзљВЪКчЁЃ”
БОЭјзЂУїЁАРДдДЃКББУРЙКЗПЭјЁБЕФЫљгазїЦЗЃЌАцШЈОљЪєгкББУРЙКЗПЭјЃЌЮДОБОЭјЪкШЈВЛЕУзЊдиЁЂеЊБрЛђРћгУЦфЫќЗНЪНЪЙгУЩЯЪізїЦЗЁЃЮЅЗДЩЯЪіЩљУїепЃЌБОЭјНЋзЗОПЦфЯрЙиЗЈТЩд№ШЮЁЃ ЗВБОЭјзЂУїЁАРДдДЃКXXXЃЈЗЧББУРЙКЗПЭјЃЉЁБЕФзїЦЗЃЌОљзЊдиздЦфЫќУНЬхЃЌзЊдиФПЕФдкгкДЋЕнИќЖраХЯЂЃЌВЂВЛДњБэБОЭјдоЭЌЦфЙлЕуКЭЖдЦфецЪЕадИКд№ЁЃ
БъЧЉЃКУРЙњgay
ЩЯвЛЦЊЃКУРЙњжјУћЕФвєРжНБЯюжЎУРЙњвєРжНБ... ЯТвЛЦЊЃКЁОФЩХСЯЕСаСљЁПЃКRealmОЦзЏЕФДЋЦц...